我們知道:一個政權的基礎是經濟,經濟穩了,政權自然穩。而貨幣作為經濟運行的基本價值尺度和交流手段,其穩定與否又直接決定了經濟的起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政權要穩定,首先要貨幣穩定。這方面可謂史有明鑒。
中國清朝可以說是亡于鴉片戰爭,而鴉片戰爭所以爆發則是白銀作祟。清中葉中國的一億人口人均白銀擁有量2—3兩,這些白銀是中國人拿自己生產的商品換來的,而人家的銀子只是從礦里開出來的,並沒有附加生產制造能力,所以,明末清初的貿易順差,只是帳面繁榮,我們是用本國的生產能力換回了大量的他國自然資源,而這種自然資源幾乎只有流通作用。因為中國缺少銀礦,而中國政府在宋朝發行紙幣失敗(政府對紙幣無兌換信用),所以在流通貨幣不足,海外貿易發展的現實下,接受其它國家用白銀支付以滿足國內流通貨幣要求,並且其它國家也沒有產品可以提供給中國,除了銀子。到后來,其它國家發現連本國銀子也不夠用了,因為進了中國就出不來,就想出來用鴉片作為商品換出中國白銀。這不能怪英國人無恥,實在是中國人只進不出,全球白銀被中國以吸銀大法吸入中國,中國人又不肯用白銀采購國外的現代工業品—鐵路,機車,紡織機械等。雖然在清初,中國仍然保持著較高的白銀流入,但到了1808年白銀流入停止了。歐洲在和中國的貿易中始終處于巨額逆差,白銀源源不斷地從歐洲流入中國,歐洲因此出現嚴重的白銀貨幣短缺。為了平衡巨額逆差,使白銀重新回流,英國政府只好向中國出口中國人需要的“鴉片”,這就是鴉片貿易的起因。鴉片貿易使清朝的白銀迅速外流。1790—1838年間,輸入中國的鴉片達440576箱,價值24000萬兩白銀。白銀外流導致銀價從1821年的每兩1000文上漲到1838年1300—1600文。白銀外流引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而戰爭賠款(2100萬元合1476萬兩白銀,1:0.71)進一步使白銀外流。從此,中國淪為買辦資產階級為主導的奴隸制金融殖民地。據統計,自1840—1915年的75年間,中國白銀外流達到12.5億兩。晚清政府同樣國庫空虛,最后經由胡雪岩向洋人六次借款,累汁金額為1870萬兩白銀才籌措到收復新疆的軍費。而中國,也正是自1840年經歷了百年屈辱史。而它的伏筆,埋在清朝繼承了明朝即將淘汰的銀本位制度。
二戰時日本失敗原因很多,但其貨幣上的原因也不可忽視,早在1931年時,日本就將其國民經濟轉向戰時經濟軌道,軍費開支從1931年的4.6億日元,占整個國家財政預算總支出的30%,增至1935 年的10.3億日元,占國家財政預算總支出的46%。在由和平型經濟向戰爭型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日本相繼頒布了重要產業統制法、工業組合法、汽車制造業法等一系列法令,確立了準戰時體制。通過國家投資、政府貸款、強制卡特爾化、軍事訂貨、貿易保護政策,促進與軍事工業有關的重要工業的發展。同時,日本從30年代起推行赤字財政政策,開始了所謂“高橋財政”的通貨膨脹政策(高橋是清曾長期擔任日本大藏相,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推行以赤字財政為主要內容的通貨膨脹政策),為日本軍事工業的發展積累資金。到1936年底,日本國債已超過 100億日元(相當于當年日本國民總收入的68%),日元與美元的兌換率從1930年的0.5比1跌至1933年的0.257比1,日元大幅貶值。同時,戰時日本政府為籌措經費發行了大量赤字公債,其所發行的國債總額,戰前的1940年為286億日元,戰敗時的1945年增長到1399億日元戰后,《日本經濟新聞》的記者,有一次在采訪賀屋興宣(1888-1977,全面侵華戰爭的近衛文??內閣與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東條英機內閣的大藏大臣,理財聖手)的時候問了一個問題:“日本的國家預算從1941年的86億日元到1945年飛漲到了235億日元,這個預算是怎麼做出來的,從哪兒來的錢?”賀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淡然:“哪兒來的錢?印唄,只要印刷機沒問題,你要多少錢都有。”照說,在濫發通貨而同時物資嚴重匱乏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通貨膨脹,可在賀屋興宣任上,還就沒有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其原因是:在統制經濟的條件下,做到不使物價上漲也非常簡單,只要不讓消費者手中有錢,沒有了通貨,也就沒有了膨脹,只要能夠把濫發下去的那麼多紙幣吸收回來就行。賀屋的方法是開展一個“愛國儲蓄運動”,讓所有人把剩余的錢都存到銀行里,去支援“大東亞聖戰”。這樣,大家既有了擁有金錢的滿足感,還能為支援了國家而感到自豪,最重要的是這筆錢已經從市場上消失,不用再擔心通貨膨脹了。然而,日本到底還是因為實質上的日元貶值而無法支持這場戰爭。
至于國民黨,就更是因為濫發貨幣導致幣制紊亂而一敗涂地。1935年11月4日國民政府宣布實施法幣法案以后,法幣成為國民政府統治區流通中的統一貨幣。抗戰期間由于法幣發行量不斷膨脹,致使物價飛漲,幣值一落千丈。到1948年8月,法幣流通量已達到640萬億元,為抗戰前1937年6月的45萬倍,法幣的信用完全破產。為了挽救由于法幣破產所引起的國民經濟崩潰的局面,1948年8月19日國民政府公布了《財政緊急處分令》,同時發布了包括《金圓券發行辦法》、《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在內的一系列財政金融法規。在《金圓券發行辦法》中,規定發行20億金圓券為本位幣,限期以金圓券1比300萬的比價兌換法幣。明令實行金圓券幣制,“限期收兌人民所有之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蔣介石在9月6日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紀念周上大罵許多持觀望態度的商業銀行“自私自利”,“直接破壞政府戡亂救國的國策”。他威逼金融實業家們必須馬上改變觀望態度,否則“不得不采取進一步措施予以嚴厲制裁。”他委派長子蔣經國為上海經濟管制特派員親臨督陣,擺出不獲全勝決不收兵的架式。 為確保金圓券發行后的流通信譽,蔣經國專門成立了近2萬人的“打虎隊”,先后查封扣押了一大批從事走私、套取官價外匯、哄抬物價牟取暴利的違法經營公司和大小老虎,將上海灘有一定影響的戚再玉、陶啟明、張尼亞、王春哲4個“小老虎”槍斃,將64個“中老虎”拘押,就連杜月笙的大管家萬墨林也被關進了大牢。雖如此,四大家族的利益並未受到影響。社會輿論評論:大老虎不打,則“小老虎死得太冤枉”,“中老虎牢中要叫屈”。杜月笙更是公開揭露孔令侃的揚子公司大量的違法活動,要求小蔣“一視同仁給予查處”。在社會壓力下,蔣經國只好派出“打虎隊”對揚子公司進行查封和清算。孔令侃見勢不妙,便急忙趕往南京向姨媽宋美齡求救,宋美齡聞訊后立即飛扺上海,要求小蔣手下留情,取消對揚子公司大案的查處。結果雙方發生了爭吵,宋美齡見調解無望,便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打到東北前線蔣介石的指揮部。接到夫人的電報,蔣介石只得扔下指揮棒趕飛上海,一見面就訓斥蔣經國“干事太露!過火!”並勒令小蔣立即停辦揚子公司一案,將孔令侃救出。此事不僅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使金圓券出籠不久就信譽掃地,而且也大大寒冷了前方將士的心。更關鍵的是:由于金圓券和法幣一樣,沒有其他貨物做準備,再加上國民政府統治區的日益縮小,財政赤字的繼續增長,致使金圓券的幣值迅速下降。僅到同年11月10日,在不足兩個月的時間內,金圓券的發行量已經突破二十億元的限額。11月11日,國民政府又出台了一個《修改金圓券發行辦法》,宣布金圓券的發行總額將不以20億元為限,而“另以命令之”。 此后,金圓券的發行量就像洪水決堤,迅速膨脹。到11月底已超過30億元,12月超過80億元,到1949年4月又超過1900億元,到5月18日,金圓券發行總額已達到98041億元。在短短9個月的時間內,金圓券幾乎成為廢紙。到了1949年6月,金圓券在廣東、廣西、江西、貴州和西北各省均被拒用,國統區經濟陷入全面崩潰,而蔣介石利用“金圓券法案”上演的幣制改革鬧劇,卻搜刮了巨額財富。據資料統計,蔣介石潰逃前夕運往台灣的黃金就有92.4萬兩、外幣8000多萬美元、銀元3000多萬元。而此時的金圓券已成為無人要的一堆廢紙,這場荒唐的金圓券幣制改革出台僅僅9個月就宣告徹底破產。金圓券法案的實施,不僅沒有挽救其反動統治,反而加速了蔣家王朝的垮台,使金圓券發行短短9個月便徹底崩潰,成為世界上最短命的貨幣。
貨幣上的胡作非為,直接動搖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當時有人這麼講到:數以億計的人民,在身體上、在財產上,都遭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損失。人民已經經歷到他們從未經歷過的可怖的景象。他們不僅早已喪失了人生的理想、創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興趣,這次,又喪失了他們多年勞動的積儲,並更進一步被迫面臨死亡。而當大多數人民都面臨死亡之際,政權實際上也在面臨死亡。
前蘇聯也是這樣的例子。1991年,蘇聯已經面臨重重危機。金融危機、國家財政收入減少、預算赤字增加,這些都迫使印鈔機加速運轉。當時蘇聯的鈔票發行量創造了幾十年來的最高紀錄。1991年蘇聯解體時,其通貨膨脹率已高達168%。由于貨幣原因引發的政治危機也愈演愈烈,國家政權搖搖欲墜。當時的國家領導人甚至想用政治作交易換取一些資金,例如答應與韓國建交,以換取其5億美元的貸款。甚至還發生這樣的事:政府竟然在未經儲戶同意的情況下提取單位和公民存在對外經濟銀行的外匯存款,其中甚至包括戈爾巴喬夫本人在國外出版書籍而獲得的外匯(當然,他本人也許不知道此事)。但是,外匯仍不夠用。蘇聯的涉外銀行無法按時支付進口商品的貨款,不少輪船因拖欠貨款和停泊費用而被扣押在外國港口。當時政府各部門之間往來信函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在國外的蘇聯專家怎麼辦?因為沒錢給他們發工資,也沒錢讓他們回國。1990年底至1991年初的幾個月中,蘇聯領導人處于兩難之中:不使用武力就無法保護整個國家,而只要動用軍隊就無法獲得西方的經濟援助。西方與蘇聯的關系越來越冷淡,蘇聯的外匯、財政問題尚未解決,又急需西方的貸款,于是只好讓步。1991年,發生了煤礦工人大罷工事件。工人要求總統辭職。罷工導致煤炭減產1500萬噸。在強大的壓力下,戈爾巴喬夫決定與1991年1月對立陶宛動武事件劃清界限,這實際上是發出了明確信號: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成為既成事實。這是戈爾巴喬夫的無奈之舉,因為嚴重的財政危機限制了蘇聯政權的自由行動。1991年春天,戈爾巴喬夫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已經無法用武力保住整個蘇聯了。1991年3月至7月發生政治突變,各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達成共識,準備改變蘇聯的國家體制。在隨后舉行的新奧加廖沃(蘇聯總統在莫斯科郊區的官邸之一)談判中,戈爾巴喬夫對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作出重要讓步,同意把蘇聯的國名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改為“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這意味著蘇聯作為統一國家的歷史已經結束。
正面的例子當然也有。比如英國。1815年在滑鐵盧擊敗拿破侖,英國最終取得這場百年長跑的勝利,坐上了歐洲霸主的寶座。這一時期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種“中心-外圍”構架,位于這一體系中心的英國家擔負著提供國際貨幣的職能,而中心國家向外圍國家輸出貨幣過程的對立面,就是外圍國家向中心國家注入資源的過程。換句話說,外圍國家以支付國際鑄幣稅為代價,獲得了使用國際貨幣的便利。此時,英國因勢利導,建立貨幣局制度,在殖民地貨幣局制度下,中心國家就是宗主國,外圍國家就是宗主國的殖民地。外圍國家需要使用貨幣,首先需要獲得宗主國的貨幣,然后以宗主國的貨幣為準備金,發行本國貨幣。這樣,宗主國的貨幣就隨著其殖民擴張而擴張了。盡管這種殖民擴張活動有多個歐洲國家都在進行,但毫無疑問,英國是近代全球最大的殖民帝國。到20世紀初,世界領土被瓜分完畢,英國所占份額最大。1876年時它已擁有22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地和2.52億人口,到1914年增加到33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地和3.94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相當于英國本土的137倍和人口的8倍多,成為名副其實的“日不落帝國”。而英鎊,則伴隨著米字旗在全世界高高飄揚,擴張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成為當時的全球通行証——世界貨幣!
有意思的是,英國的衰落也與英鎊衰落同步:二戰期間,德國對付英國的武器並非只有坦克、大炮和飛彈,還有比這殺傷力更可怕的,那就是——大規模的、近乎完美的假英鎊!其方法是大量制造英鎊假鈔,通過大量偽造英鎊造成英鎊貶值,引發公眾對英鎊的信心危機,從而打擊英國經濟,這個想法最先是由德國刑警頭子阿圖爾·奈比提出來的。1939年9月,這個想法得到了黨衛軍帝國中央保安局局長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大力支持。海德里希向希特勒報告了偽鈔制造計劃,得到了批準,但希特勒只支持偽造英鎊,不允許偽造美元,他說“我們現在還沒有和美國人打仗呢”。 本哈德行動制造了數量驚人的假鈔,造成了英鎊大幅貶值,沉重打擊了世界各國對英鎊的信心,加速了英鎊讓位于美元世界貨幣地位的進程。
今天的中國,通貨膨脹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只要想一想今天人民幣1元前與二十年前人民幣1元錢的購買力的比較,就不難明白這一點。而幣制的紊亂,通貨膨脹的加劇將導致什麼結果,則歷史已有結論。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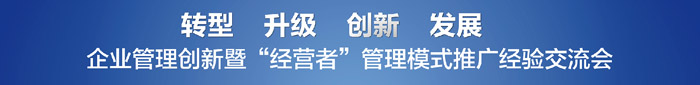
.bmp)

.bmp)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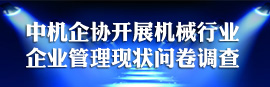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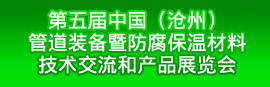
(3).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