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能機時代,從1998年科健產出第一部國產品牌的中文數字GSM手機開始,以科健、波導、熊貓、迪比特等為代表的第一代國產手機品牌,在毫無經驗和技術積累的情況下,從貼牌起家,竟從摩托羅拉[微博]、諾基亞[微博]等實力雄厚的手機大鱷手中“硬生生打下半壁江山”——據原信息產業部的數據,1998年到2003年的短短五年間,國產手機在國內市場的份額從零攀升至55%。
然而,那一批國產手機在2003年從巔峰跌落,最終塵歸塵、土歸土。過山車般的劇情至今令人唏噓。
牌照和貼牌
時間回到30年前。
1984年,隸屬于中國科學院的科健在深圳成立。彼時,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橋頭堡的地位剛剛確立。為支持深圳的對外開放,以中科院、原電子工業部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央部委及國企在深圳成立電子工業企業,科健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成立伊始,科健即以振興民族通信工業為己任,立志生產世界一流的中國手機。然而,這個響亮口號喊出之后,是整整14年的沉寂。
在這期間,洋品牌進入中國市場。
1987年,隨著重達一公斤的“大哥大”——摩托羅拉3200漂洋過海來到中國,這家老牌通訊廠商也正式在中國設立辦事處布局移動手機業務,成為最早涉足中國市場的外國手機品牌。此后,愛立信[微博]、諾基亞等一大批國外手機品牌陸續進駐中國。
1987年開始的十年間,洋品牌已占據了中國市場90%的份額。這終于令有關部門產生了危機感。
1998年,原國家信息產業部和原國家計委出台了《關于加快移動通信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要求手機生產必須獲得其牌照許可。文件還規定,在華外資企業生產的手機必須有60%銷往海外市場。
這是對國產手機的一種赤裸裸的扶持。
1998年10月,科健終于推出其手機產品——科健KGH-2000。盡管被諷刺為“不入流”,但這畢竟是中國第一部國產手機,其意義遠超過了產品本身。
此時,手機牌照是所有資源中最稀缺的。由于政策保護,加上巨大、空白的市場,首批拿到牌照的國產手機廠商——科健、熊貓、南方高科、廈新等開始強力進入,在洋品牌的山頭中攻城拔寨。
國產手機的崛起,與兩個關鍵詞密不可分,一是牌照,二是貼牌。
“當時手機是新興行業,勢頭很猛,但基本上都是把別人的整機拿過來,貼上我們的標簽而已,這一招是當時非常常見的拿來主義。”深圳市手機行業協會會長孫文平告訴《幣望東方周刊》。
受阻于中國手機市場準入機制的洋品牌們,只好向持有牌照的中國伙伴伸出橄欖枝,借道而行。
2002年,三星[微博]與科健達成合作協議,合資成立深圳三星科健移動通信技術有限公司,專門生產三星的CDMA手機。作為回報,三星每年將提供給科健數款機型用于貼牌生產,雙方約定,三星不得在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本土市場銷售同款機型。
“手機中的戰斗機”波導也選擇了同樣的路徑。以傳呼機起家的波導憑借在國內市場的巨大號召力,在1999年與法國SAGEM公司簽訂合作協議,進行移動電話技術開發和生產合作。SAGEM借助波導的手機生產牌照打入中國市場,波導則通過貼牌生產手機賺取利益,兩者各取所需。
死磕出來的產業鏈
2000年,TCL[微博]推出第一款國產WAP手機TCL999DW;次年推出鑽石手機,將通訊工具與裝飾品相結合,領一時風尚。2003年,TCL手機以9.31%的市場綜合占有率穩居國產手機第一,位列全球第八。
“那時候經銷商派人長年蹲守在TCL工廠外面,一有貨就要,有多少要多少。為爭取貨源,他們甚至搶著往我們賬上提前打款。”深圳市聯代科技有限公司COO周軍林回憶說。他曾在TCL手機業務負責供應鏈。
但是,TCL這條路並不好走,因為它並沒有選擇貼牌模式,而是選擇了自己研發。
“TCL手機可以說是國產品牌中第一個投入力量搞研發的,自己生產,自己組織供應鏈。”周軍林說。
自己制造手機的結果異常慘烈。
“供應鏈都掌握在外資廠商手里,我們連做手機外殼的塑膠廠都找不到,不管怎麼懇求都不肯給我們做,就是那麼牛。”周軍林回憶說。
于是,TCL只有使用那種給啤酒瓶或者塑料瓶噴漆的生產線,其結果就是,用手一抹,漆就會掉。
“現在做手機開套模只要幾萬元,可那時我們出200萬元都沒人願意做。”周軍林說。
簡陋、殘缺的產業鏈,直接導致手機質量差。周軍林告訴本刊記者,TCL曾有一種元器件,買了幾千萬元來供維修之用。故障率之高可見一斑。
“那時候別說核心技術,就連一個塑膠殼都被外資壟斷,我們是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自己培養出了供應鏈。雖說有一些質量問題,但這是無法跳過的一步。沒有當時的死磕,深圳就不會有今天如此完善的產業鏈條。”周軍林說。
2002年的深圳,已經顯示出成為中國第一手機制造基地的實力。
在當時的17個國產品牌中,深圳占了5個——科健、康佳、國威、天時達、中興。當時國產手機年產量在2000萬部左右,深圳占700萬部。在那一年,科健的產量約300萬部,康佳約為200萬部。國威、天時達、中興三家企業共200萬部左右。
同時,深圳還是洋品牌手機的重要生產基地。深圳桑菲公司即是飛利浦手機的生產基地,當時共建成了四條手機生產線。2001年,飛利浦關閉了中國以外的其他手機生產線,大部分轉移到了深圳桑菲公司。
如果把國產品牌和洋品牌加在一起,當時深圳的手機年產量在1500萬部以上。這對于整個產業鏈條的完整和完善至關重要——一部手機有300多個零部件,除了核心元器件,從顯示屏到電池,從模塊到電池板,從微電機到電阻電容,深圳都能就地配套。這在中國甚至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
一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比亞迪(50.41, -1.19, -2.31%),當時其日產手機電池30萬塊,年產手機電池1億多塊,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機電池制造企業。
第一批國產品牌倒下
2003年,在經歷四年的快速增長后,國產手機銷量開始下滑。
數據顯示,科健手機2003年上半年的出貨量僅93萬部,比2002年同期下滑了51%;主營業務收入10.34億元,比2002年同期下降18.62%。這樣的業績不僅讓還在跟三星“度蜜月”的科健傻眼,也讓處于亢奮中的國產手機同行為之一凜。
曾經風光無限的科健仿佛一夜之間黯然失色。不過,在眾多業內人士眼中,科健的“滑鐵盧”遲早要來——其最初在國內市場的勢如破竹,依靠的是消費者對于民族品牌的親近感,及其產品宣傳的不遺余力。
其最初引以為豪的國產機技術,隨著產業發展劣勢盡現,尤其是在與三星合作后,科健放松了技術研發,僅滿足于貼牌帶來的豐厚效益,最終淪落為一家機械生產的“代工廠”。
然而,科健的衰落僅僅是風暴的序幕。
波導手機2004年第一季度主營收入和利潤都有兩位數的降幅,而就在2003年上半年,波導手機銷量達337萬部,超越了摩托羅拉和諾基亞,成為市場第一。
在市場份額上,本土手機企業也出現潰敗跡象。
市場研究機構賽諾公司的數據顯示,2004年第一季度,波導的市場份額萎縮了1.7%,其第三的位置被三星替代。而此前名不見經傳的愛立信,2004年的市場份額已與夏新相近。
從2003年下半年到2005年年初,國產手機的整體市場份額由此前的55%下滑至44%。
“2004年是下滑期,2005年已經大規模虧損。”金立手機執行總裁盧偉冰告訴本刊記者。
科健最終沒能挺住。到2004年中期,存貨高達6.85億元,占當時主營業務收入的68%、主營業務利潤的7.5倍。2005年,科健逐漸從消費電子市場退出,曾經的國產機“第一品牌”關門大吉。
到2006年、2007年,國產手機的頹勢仍不見好轉。研究機構易觀國際[微博]的數據顯示,2007年第四季度,聯想、波導、夏新的市場份額分別是6%、3%、2.8%,市場份額萎縮嚴重。波導2007年前三季度虧損5.06億元,夏新同期虧損4.6億元,聯想手機在上個財政年度的虧損額達1.33億元。
“這一時期,因為技術上沒有優勢,國產手機之間的差異很小,嵌顆鑽石、會震動、會唱歌跳舞,就是產品的亮點。第一批國產品牌倒下,主要是因為沒有核心技術可以支撐。”酷派集團副總裁曹井升告訴本刊記者。
第二季開幕
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永遠不缺冒險者。
借助于政策放寬和技術突破,以天語、金立等為代表的第二代國產機成為黑馬。
“天語和金立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打了價格差。當時的手機是稀缺品,價格都很高,以TCL為例,當時賣到3000多元的手機,每部可以賺一兩千元。摩托羅拉和諾基亞的利潤更高。那麼天語和金立只要賺500元就好了,充分利用了中國市場的縫隙。”周軍林說。
“第一批國產手機風行一時的重要原因是當時的市場環境,包括政策條件都非常有利,那是靠機會,不是真正的實力。”在深圳手機行業從業十余年的唐強告訴《幣望東方周刊》。
2004年,延續五年之久的手機生產“審批制”終止,取而代之的是“核準制”。審批制下,獲得許可牌照的只有36家企業,其他手機制造企業只能靠貼牌度日。審批制終結,一批合資的國產手機生產商開始打出自有品牌。
兩年后的2006年,台灣聯發科[微博](MTK)迅速崛起,專門生產手機芯片,能夠把手機主板和軟件集成,手機廠商只要購買這種廉價的MTK芯片,加上定制的外殼和電池,就可以自己組裝手機。
這成為功能機時代國產手機第二波浪潮的重要推手。
嶄露頭角的國產手機中,天語最為典型。
2002年,國產手機勢頭正猛時,以手機代理業務賺得第一桶金的榮秀麗,用1000萬元人民幣注冊天宇朗通。彼時,天語被外界稱為“三無”企業——無手機牌照、無手機研發歷史、無手機生產能力。而榮秀麗更被稱為“山寨之母”。
不過,與科健、波導不同,榮秀麗不惜血本建立研發團隊,這在當時被看作是創新之舉。
然而,在虧損8000多萬元后,天語不得不與MTK合作,推出成本低廉的山寨機。
芯片技術交給聯發科,生產外包給富士康等,天語自身聚焦于銷售渠道的建立——在全國尋找代理商,交出手機定價權,以讓渡利潤換取渠道。2007年,天語手機出貨量達1700萬部,在中國手機市場僅次于諾基亞,成為國產手機冠軍。
扎根于深圳的金立,與天語成立于同一年,2005年拿到手機牌照后開始生產自有品牌手機,曾在各大電視台滾動播出的“金立語音王”就是其代表產品。隨后,2006年金立完成目標年銷售量300萬部,利潤超過2億元。
功能機時代國產手機的第二波浪潮,主角已變為天語、金立、中興、長虹[微博]、宇龍通信。
2007年,四川長虹(4.33, 0.00, 0.00%)的手機業務成為其支撐業務之一,營業利潤率僅次于彩電產品。
中國無線2007年的財報顯示,其全資子公司宇龍通信營業收入達到12.77億港元,較2006年增長99.4%,凈利潤1.67億港元,相比2006年凈利潤增長212%。而手機產品毛利率高達40.8%,即便與諾基亞等洋品牌高端手機相比也毫不遜色。
當時,中興通訊(14.24, -0.18, -1.25%)已經成為國產手機中亮眼的一支力量,2007年已成為全球第六大手機廠家,其手機業務年收入76.45億元,比2006年增長了69.16。而手機業務營業利潤率仍然維持在22.31%的行業高水平。
此時的TCL,雖成為第一代中的幸存者,然而其手機業務重心已轉型海外。2008年第一季度,其EMEA(歐洲、中東及非洲市場)和LATAM(拉丁美洲市場)兩個市場占公司總銷售額的92%。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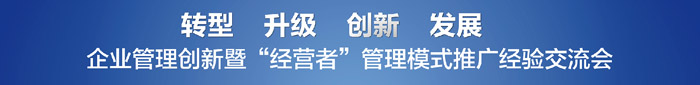
.bmp)

.bmp)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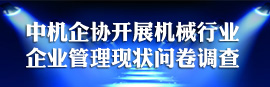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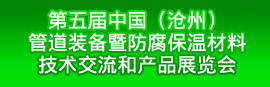
(3).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