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鐵走出去始于2010年,在經過知識產權和動車事故的質疑之后,2013年新一波高鐵出海高調開始。與剛開始不一樣的是,此次在海外推介中國高鐵的不再只是企業或者鐵道部門,中國最高領導層親自化身“高鐵推銷員”,在各種出訪場合提及這張“中國名片”。
由此,高鐵走出去更具國家意義——推動產業的升級換代,作為中國工業國際生產競爭力的一個符號,以及消化國內過剩的產能。7月25日,由中國土木工程集團有限公司承包建設的連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的高速鐵路二期工程歷時11年終于通車,這也是中國完成的第一條海外高鐵工程。
然而,海外高鐵市場未必如想象中廣闊。
高鐵是一個國家的“奢侈級”基礎設施。建設高鐵有三個較高的經濟門檻:首先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其次是人口密度要求;三是電力供應充足。能滿足這些條件,又有意願修建高鐵的國家可謂稀缺。世界銀行[微博]由此作出判斷,全球最大的高鐵市場仍在中國。
相較于能夠以經濟模型計算出來的經濟門檻,高鐵承建雙方要面對的更大不確定性在于政治風險。
兩項因素夾擊,中國曾經接觸過或有意向在海外進行的項目中,實際落地者寥寥。
小容量的市場上,競爭激烈非常。技術標準是首要的因素,給中國高鐵進入他國市場,尤其是發達經濟體設置了極高門檻。隨之而來的,中國高鐵所具備的成本優勢在海外市場也不那麼明顯。中土的項目在土耳其雖然是中國高鐵項目在海外落地的第一回,但仍然局限在土建領域。高鐵建設的車輛設備(動車組)和控制系統部分有著更高的技術水平,以及更大的附加價值。目前中國企業還未在海外建設過從工程建設直到交付使用的一攬子高鐵工程。
國際巨頭西門子、龐巴迪、阿爾斯通等企業都已形成了機車車輛、軌道通訊信號到供電系統等完整的產業鏈和系統集成能力。中國的南車、北車、通號、中鐵建等公司則是在原鐵道部體制下根據專業分工組建而成。這種情況下,中國高鐵要想走出去急需提升全面系統集成能力。
“全產業鏈”的整合正在醞釀,企業之間爭奪未來海外戰略的主動權的博弈已然開始。
高鐵是三高門檻的狹窄市場
從某種角度來說,高鐵不啻為一個國家的“奢侈級”基礎設施。多位業內人士表示,建設高鐵有三個較高的經濟門檻:首先高鐵是高造價項目,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其次是人口密度要求很高,世行研究認為線路連接城市所飽有的人口數量至少要達到2000萬,線路才有可能收回成本;三是電力供應,時速250公里的列車皆為電力牽引,耗電量巨大,而且隨著時速增加,耗電量呈階梯級增長。
能滿足這些條件,又有意願修建高鐵的國家可謂稀缺。因此一旦有項目消息放出,各大國際高鐵巨頭聞風就會派出團隊跟蹤,競爭激烈。國際鐵路聯盟UIC在2013年11月發布的報告指出,目前計劃新建高鐵的國家有日本、印度、美國、巴西、摩洛哥和幾個歐盟國家。此外,經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國政府批準的新加坡至吉隆坡高鐵預計在明年招標。
世界銀行駐華代表處高級交通專家歐杰(GeraldOllivier)對全球高鐵市場的分析是,有意向建設的國家大多仍在進行國內討論,即使新建大部分也只是建設一兩條線路連接兩個特大城市,難以像中國這般建設大規模的高鐵綱絡,“全球最大的高鐵市場仍在中國”。
據整理發現,中國目前至少曾與19個國家進行了高鐵合作或者合作洽談,其中包括土耳其、委內瑞拉、沙特阿拉伯、利比亞、伊朗、泰國、緬甸、老撾、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羅馬尼亞、巴西、波蘭、美國、英國、俄羅斯和印度。至于高速動車組的出口,至今為止只有南車中標香港的高鐵項目,該線路將連接香港和廣州。
其實,有相當一部分合作項目處在非常初始的階段,也因此各種消息眾說紛紜,前后矛盾。
緬甸高鐵就傳出過各種証實和証偽的消息。2010年12月,緬甸駐華大使館公使銜參贊萊敏吳(HlaingMyintOo)對媒體表示,連接昆明和緬甸首都仰光的高鐵將在兩個月內動工,但實際上直到2011年5月,兩國才簽署相關諒解備忘錄。今年又有消息傳出將在6月開始動工,但7月底緬甸單方面宣布備忘錄已到期,中止與中國的合作。
據梳理求証,目前已經簽約,確定2由中國承建的高鐵或準高鐵項目共有四個:中土集團承建的土耳其安伊鐵路和利比亞高鐵,中國中鐵(3.23,0.01,0.31%)股份有限公司中標的委內瑞拉迪納科—阿納科準高鐵和沙特阿拉伯的麥麥高鐵,即沙特的麥加-麥地那第一標段。安伊高鐵于8月竣工,麥麥高鐵正在建設當中。此外,利比亞項目由中土集團承建。雖然對外表示其最高時速能達250公里,但實際參與項目的工程人員表示,由于利比亞政府沒有選擇電力機車,而用內燃機車牽引,最高時速只能達到180公里-200公里,不能算高鐵。2011年,這一項目因利比亞爆發內戰停工,至今憚于惡劣的安全形勢未有重啟計劃。
委內瑞拉項目則是一個準高鐵項目,把該國農場區和石油帶所在的兩個州連接起來,最高時速220公里。項目合同簽訂于2009年,本計劃在該國2012年總統大選前完工,但拖延至今仍未完成。今年4月,這一項目的組成部分——北部平原鐵路路段正線開始鋪軌,在動工的新聞稿中,提及項目克服了委內瑞拉復雜多變的“環評困難、工會干擾、貨幣貶值、物資匱乏、治安惡劣”等等問題。就在同時期,中鐵董事長李長進在香港出席公司新聞發布會時將項目推遲歸因于融資問題;去年12月,中鐵旗下主攻國際業務的中鐵國際集團董事長甘百先曾赴委內瑞拉駐華大使館,就委國高鐵工程欠款問題與其大使溝通。
除去上述四個項目,余下15個已知中國高鐵的潛在合作對象中,符合前述三個建設高鐵條件的國家寥寥無幾。
資金匱乏是高鐵上馬面臨的最普遍問題。越南曾計劃在河內和胡志明市之間建設高鐵,預期造價為558億美元——幾乎是全年GDP的50%。2010年以花費太過高昂為由遭到國會反對;老撾國會2012年底通過了中老鐵路項目,按原計劃應為高鐵,但出于降低成本考慮改為時速160公里的普通鐵路,造價為70億美元,但這仍然幾乎相當于老撾當時一年的GDP,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都曾勸老撾政府“慎重考慮”。
即使是金磚五國之一的巴西,資金也是個很難跨越的障礙。巴西計劃建造連接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的高鐵線路,沿途城市的經濟狀況和人口密度都已達標,但自2011年開標以來兩次流標,原因是大多數高鐵公司認為巴西政府給出的盈利預期太低,目前尚不知道第三次招標何時舉行。
長距離高鐵線路的主要障礙還有人口密度。例如歐亞高鐵必須穿過人湮稀少的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才能進入歐洲,從經濟角度看沒有足夠的乘坐需求。歐杰表示,在實際操作中不會考慮建設超長客運高鐵,因為旅行時間太長,乘客寧願選擇飛機。
此外,高鐵建成后后續的維護保養都要對所在國的技術、管理水平有較高要求。中國計劃在非洲設立高速鐵路研發中心,但電力是對非洲諸國的考驗。一位長期在非洲做鐵路工程的負責人表示,非洲大部分國家電力供應不足,民用電力尚未能保障,高鐵需要的電力根本無從談起。
“我也讀到了不少中國高鐵走向全球的新聞,但我認為建設與否更多還是要取決于所在國的發展計劃和需求。能滿足三個條件的國家不算多,很多國家目前提出了計劃,但投資方面的問題解決不了,或者有電力瓶頸,有實際動作的國家沒多少個。”負責追蹤海外高鐵項目的中土集團亞太事業部副總經理吳暑林坦言,高鐵在中土集團的海外追蹤項目里所占比例並不高。
政治風險難以預期
相較于能夠以經濟模型和分析計算出來的經濟門檻,高鐵承建雙方要面對的更大不確定性在于政治風險。上世紀90年代中期,歐杰曾在非洲參與七國跨境鐵路的建設,這次經歷給他留下深刻體會:每增加一個國家,難度要增加三倍。“你不但要考慮這屆政府的需求,還要考慮未來5年-10年的政治變化。即使是時任政府,開出的條件也會根據選民需求隨時變化。”
政局變化影響高鐵建設的案例,近年來最為明顯的莫過于泰國。前總理英拉上台以后,熱衷于推動鐵路基建,在其政府規劃中,計劃在2022年前建設四條高鐵線路,將曼谷與北部彭世洛府、東北部呵叻府、西部華欣和東部芭堤雅連接起來,總長度1800公里左右。
趁此需求高漲之際,2013年10月,中國與泰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泰王國政府關于泰國鐵路基礎設施發展與泰國農產品(12.31,0.08,0.65%)交換的政府間合作項目的諒解備忘錄》,文件中指出中方有意參與廊開至帕栖高速鐵路系統項目建設,而泰國以農產品扺償部分項目費用,這一計劃為外界形容為“高鐵換大米”。
這份備忘錄的簽署並不意味著中國企業必然中標泰國高鐵項目,該項目將會進行國際招標,三井物產、三菱重工業以及JR東日本、九州旅客鐵道(JR九州)等日本企業去年成立了企業聯合會,也預備參與泰國高鐵的競標。
不過,還沒來得及與日本企業進行面對面的競爭,“高鐵換大米”的計劃就因泰國的政局變化而中止。今年5月英拉政府遭遇政變,軍政府上台,隨后泰國憲法法院判決已獲國會通過的高鐵項目違憲。僵持了三個月之后,泰國軍方最終宣布原有的高鐵計劃改為普通鐵路的改造和提速,改造后為最高時速160公里的復線寬軌鐵路,線路設計也發生了變化,和中方的合作要重新進行談判。7月底軍政府曾派外事顧問到中國表達了在基建項目方面的合作意願,但迄今為止泰方尚未宣布要就鐵路改造進行國際招標或與中國合作的消息。
除了泰國之外,中國連接東南亞的其余高鐵線路也遭遇了類似問題。中國計劃推動泛亞鐵路的建設來實現與東南亞國家的互聯互通。泛亞鐵路規劃以雲南省為中心輻射,包括三個方案:東線方案需要經過越南,具體為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金邊、胡志明市、河內到昆明;中線方案經過老撾和泰國,從新加坡、吉隆坡、曼谷、萬象、尚勇、祥雲到昆明;西線方案則要通過緬甸,從新加坡、吉隆坡、曼谷、仰光、瑞麗到昆明。
出于地緣政治安全考慮,越南在統一軌道寬度的問題上一直不肯讓步,再加上今年中越之間領土糾紛不斷,重啟連接兩國的高鐵項目困難重重。
“由于緬甸政治在過去兩三年里發生了巨大變化,泛亞鐵路的西線建設也停滯了。”高柏表示。中國一直在境內推進中緬鐵路(昆明─緬甸皎漂,時速170公里-200公里)的建設,每逢雲南沿線路段、隧道或者配套公路的開工和完工,總會傳出泛亞高鐵或者中緬鐵路已經動工的消息,實際情況卻是緬甸方面一直未有動作,直到今年緬甸單方面宣布與中方簽訂的三年合作備忘錄已經到期,取消中緬鐵路的建設計劃。這是自密松水電站之后,緬甸實行民主化改革后雙方中止的第二個基建合作項目。
老撾所遇到的國內政治阻力最小,但對它來說需要解決的是鄰國的壓力。2012年底,老撾國會表決通過了醞釀六年的中國-老撾高鐵項目,但至今仍未動工,主要因為該段上游的泰國段沒有確定,中國對老撾的貸款也無法落實。此外,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王士錄曾表示,與老撾關系密切的越南以這個項目“威脅到越南的國家安全”為由,強力阻撓老撾實施該項目。
中國高鐵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還遇到了一些較為隱形的政治風險。羅馬尼亞高鐵項目目前已經遞交歐盟審批,2013年李克強總理訪問該國時也和對方政府確定了在高鐵領域的合作意向,各中國高鐵建設公司都開始對項目進行追蹤。一位負責跟蹤羅馬尼亞高鐵的某鐵路建設公司項目經理表示,他們曾經和羅馬尼亞政府高層開會商討該項目,但感覺對方顧慮很多。“羅馬尼亞作為前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變化還不徹底,(談項目時)可變的因素很多。”
不可否認,高鐵等基礎設施建設關系到所在國家的發展大計。“不修鐵路就沒有發展,不帶動(經濟發展)和創造就業,社會和國家就無法穩定,即使在政治上經常換人,但是(業主國)總的目標沒變。”王夢恕對政治風險較為樂觀;不過歐杰也提醒,部分國家政治環境變化太快,中國企業要有心理準備,國外的高鐵建設不會像中國的高鐵政策般穩定。
中國高鐵標準尚未得到廣泛認同
歐杰的辦公桌上擺著一本厚厚的白皮書,里面匯總了與中國高鐵有關的各種標準並已翻譯成英文。不過這並不是中國正在力推的“中國高鐵標準”官方版本,“這是世行研究組自行搜集的資料,而且可能還並不完整”,歐杰解釋。
在高鐵的基建方面,主要涉及勘察、設計、施工、驗收及其他相關的建設規范和標準。得益于先發優勢,西方標準至今在全球高鐵領域占據主導地位。曾被歐美殖民過的國家,其鐵道系統尤其是軌距采用的基本是宗主國的標準。后來西方國家率先研發出高鐵之后,大力補貼本國的咨詢公司進行可行性報告和設計,逐漸用美標、歐標占據了這塊新的全球市場,尤其是被殖民的國家都已經采用了這些標準,想要引入新的標準體系相當困難。
正因如此,推行高鐵的“中國標準”也屢屢見諸于領導人的講話之中。合同總額為83億美元的尼日利亞鐵路現代化項目就以全部采用中國鐵路技術標準建設為傲。
委內瑞拉的準高鐵項目采用的也完全是中國標準。按照合同,該項目采用中國的技術標準,從中國進口主要工程材料、機車車輛、工程設備和施工設備。中鐵負責鐵路工程的設計、采購和施工,雙方還將成立貨車車輛組裝廠、軌枕生產廠、道岔組裝廠和鋼軌焊接廠共四個合資工廠,中方將對委方進行技術轉讓,對主要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進行培訓。
在基建方面,中國高速鐵路的規范和標準目前仍然與普速鐵路共享很大一部分。這上百個標準和規范十分零散,分別由原鐵道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鐵道部建設司、原鐵道部經濟規劃研究院發布,沒有統一收錄在一起的版本,也沒有翻譯成英語。
這讓中方鐵路基建人員很難向外方解釋所謂的“中國標準”。吳暑林以自己的經歷總結:“全球市場對中國標準了解有限,此外中國標準建造的高鐵如何與業主國已有的鐵路綱絡兼容、配套是個難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訴求。”
進軍新興發展中國家,中國標準尚有一搏的空間。但要想打開發達國家市場的大門,遵從當地的高標準幾乎是鐵律。
在已經建成的土耳其安伊高鐵項目上,雖然土耳其自身仍在進行歷時長久的加入歐盟談判,但其工程建設已經要求采用歐盟標準,這意味著中國高鐵所有的產品裝備和施工設備都要有歐盟認証,包括水泥、鋼軌等,其中最為重要的信號系統只能在獲得歐盟認証的六家企業中采購。此外,設計規范、施工流程及監管也要遵循歐盟的標準。
對于中鐵、中鐵建這樣的總承包商來說,在認証方面所遇到的挑戰非常分散、數量巨大。“我們是沖在最前頭的,僅僅靠我們一個企業是很難做到的,包括軌道、道岔、電力電器化、信號都有相應的廠家和安裝商,是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如果沒有歐盟認証,那我們也走不出去。”吳暑林表示。
不過在高鐵產業鏈上的制造企業在這方面的熱情並不高。要通過歐盟的認証,不僅要繳納高昂的認証費用,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一個普通的高鐵原材料,歐盟認証至少需要花兩年到三年的時間,再加上需要將樣本送到歐洲相關實驗室檢測,耗資不菲。目前中國在西方發達國家進行的高鐵工程寥寥無幾,因此高鐵相關企業缺乏申請西方認証的熱情,更多的中國企業願意將注意力放在國內的高鐵市場上。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最容易走出去的應該是車輛,因為操作相對比較獨立和簡單,可直接中國制造或者當地設廠制造移交。但在這方面,中國的“高鐵標準”同樣復雜。
中國高鐵發展之初,原鐵道部用市場換技術並同時鼓勵南車、北車進行吸收研發,日本川崎重工、法國阿爾斯通、德國西門子、加拿大龐巴迪的產品和技術分別被南車、北車引進,因而產生了四個高鐵型號及其對應的技術平台。CRH1的生產方是加拿大龐巴迪公司與南車所屬青島四方的合資企業BSP;CRH2的生產方是南車所屬的南車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技術源自川崎重工;CRH3的生產者為北車旗下唐山機車車輛廠,與德國西門子合作;CRH5由北車所屬的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與法國阿爾斯通公司合作生產。
這種“四方割據”的局面對于中國動車組的部件標準化、平台一體化是很大的阻礙。9月1日,中國鐵路總公司組織召開了中國標準動車組設計方案評審會,其表示將在兩年內分階段研制時速350公里的中國標準動車組。
高柏表示,中國高鐵想“走出去”,必須打破先發國家通過設定國際標準對中國高鐵的標準封鎖。“有媒體報道日本四家高鐵公司已經聯合成立了國際高鐵聯盟,下一步將聯合歐盟和美國,要制定共同的國際高鐵標準,這是針對中國而來的。”他認為破解之道是學習華為的市場策略,從落后國家入手,繞開那些已有自己高鐵標準的發達國家。
國內成本優勢海外難復制
世界銀行在最新研究報告《中國高速鐵路:建設成本分析》中指出,中國高鐵建設成本僅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中國建設時速達350公里的高鐵,每公里基礎設施單位建設成本通常為1700萬至2100萬美元,而歐洲的高鐵每公里的建設成本為2500萬至3900萬美元,而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可高達5600萬美元。
成本優勢是中國高鐵走出去時,最經常使用的一塊招牌。以往的基礎設施承包經驗也表明,這在非洲、拉丁美洲等欠發達、資金又較緊缺的國家確實往往能幫助中國贏得生意。不過,目前已經敲定的四個高鐵出海項目,勝出的原因並非都是低價優勢。
陳志杰此前代表中土集團負責利比亞項目,他表示利比亞項目是以議標方式獲得,主要得益于中國政府此前和利比亞良好的外交關系。
安伊鐵路在2005年進行競標時,中土集團與負責籌款的中國機械進出口(集團)公司,以及兩家土耳其公司組成了一個聯合體,競爭對手還有30多家包括來自土耳其當地、日韓和德國的公司組成七個聯合體。中土集團的聯合體最終以12.7億美元的價格中標。
中土集團亞太事業部副總經理吳暑林表示,在競標過程中,中國所在聯合體所提出的工程造價並不是最低的,但由于中方提供了7.5億美元的混合貸款,其中包括5億美元的優惠貸款,最終在經濟評價中勝出。對于急需基礎設施又囊中羞澀的業主國來說,中國豐厚的資金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優勢。
如今中國鐵路在“走出去”的時候大多數都附有利率優惠的中國貸款。北京交通大學經濟學教授趙堅認為,貸款最終必須償還,如果該國沒有支付能力,而項目本身又不具有盈利性,無異于浪費了中國的投資。但中國高鐵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高柏指出,高鐵出海有戰略意義,不應該單純計算經濟賬。被稱為“鐵路系統代言人”的工程院院士、中鐵隧道集團副總工程師王夢恕也認為,可以“用資源換高鐵”。趙堅則對類似觀點不以為然,“用大米換高鐵,100年也換不回來”,“如果是遵循以往援建非洲鐵路的模式,那麼建普鐵即可,為什麼要建昂貴的高鐵?”
現實中,越來越多的國家對于中國資金也並不是“來之即收”,高鐵這類基建項目對于當地政府來說也有更多造福本地經濟的需要。
中國曾表示願意參與連接倫敦與英格蘭北部HS2高鐵的建設,但《金融時報》引述英國官員的話稱,中國方面不會直接參與由英國納稅人埋單的鐵路建設工程。這意味著,中方只能投標申請連接倫敦與英格蘭北部HS2高鐵的運營權,或投資于沿線的外圍項目,如車站周圍的開發項目。
更多國家對于中國相關項目的本土化程度進行了嚴格的界定。2013年,南車中標南非國家交通運輸集團有限公司(Transnet)的訂單,為南非鐵路改造項目提供95台全新普貨電力機車,其中85台都被要求在南非生產制造。南非駐華大使蘭加介紹:“所有要在南非投資的企業應在建設和制造活動中注意保証采用本土原材料和勞動力。本土材料所占比率需要達到60%,對本地勞動力僱傭也有相應要求。”
世界銀行的研究顯示,高鐵在中國造價較低的因素包括低征地成本、低價勞動力和規模優勢。這三項在國外均很難實現:外國的土地多為私有,征地費用高昂;勞動力方面,業主國家對使用本國勞動力的比例有嚴格要求;只建一兩條高鐵,就無法對各項建設內容實行標準化設計,建立富有創新性和競爭力的設備制造和土建工程的產能,以及在多個項目上攤還土建設備的資金成本。
歐杰認為,相較于老牌高鐵國家,中國在海外從事高鐵基建項目,主要的優勢是擁有眾多經驗豐富的工程管理人員和工程師,以及這些人員的人力成本較低。
安伊高鐵的結果也証明,中國高鐵的低成本優勢在國外不能完全復制。
中土集團在項目中標后,業主在合同中並沒有說明要求從哪個國家采購,中土集團就與眾多合作過的中國企業,其中包括鋼軌、道岔、電力電氣化的接觸綱、接觸線、變壓器等簽下采購合同。然而在之后的技術交流中,土耳其方面指出其產品都未經歐盟認証,中土集團被迫違約重新從奧地利、意大利和德國等國采購。最終在這個項目上,中土集團只使用了大約5%的中國設備和原材料。再加上工程延期和線路改變等因素,工程最終耗資比報價高出40%。
不過,利潤並不是中土集團參與這個土耳其項目的初衷。中土集團總經理助理、高級工程師鄭建兵曾對媒體表示,他們基本“按零利潤”的想法來進行這個項目。最寶貴的收獲是打開歐洲市場大門的一把鑰匙。只要再過兩年安伊高鐵的保質期結束,他們即可獲得在歐洲施工的經驗認証。吳暑林說,“我們目前是中國唯一一家(企業)能拿到這個經驗認証的。在歐洲做高鐵,除了有標準門檻,在歐洲做過工程的經驗也是必要條件。”
因此中土集團計劃將進一步參與土耳其其他高鐵線路的競標,土耳其目前計劃建設從東部卡爾斯省到西部埃迪爾內省長達2000公里的東西線高鐵。經驗認証對中土集團參與未來波蘭、波羅的海三國以及羅馬尼亞的高鐵招標也至關重要。
中土集團耗時11年、耗資超過17億美金的項目雖然是中國高鐵項目在海外落地的第一回,但仍然局限在土建領域,而高鐵建設的車輛設備(動車組)和控制系統部分有著更高的技術水平,以及更大的附加價值。目前中國企業還未在海外建設過從工程建設直到交付使用的一攬子高鐵工程。中國高鐵出海,仍然任重而道遠。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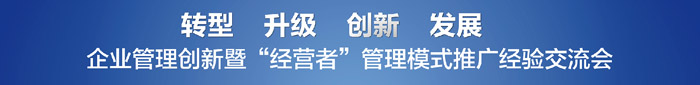
.bmp)

.bmp)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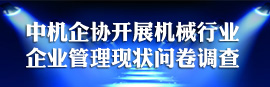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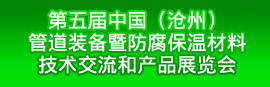
(3).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