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李東生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互聯綱+”與TCL在一年前提出的“雙+”轉型,不謀而合。
無論是從業務布局還是從經營模式來看,中國消費電子企業中,與三星最為接近的莫過于TCL集團。事實上,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也每每將三星視為自己公司的對標對象。
盡管近年來TCL的彩電、手機、面板等業務奮起直追,整個集團2014年的營收也首次突破1000億元大關,然而不得不說,面對標兵,TCL的追趕還是很辛苦。
以2014年的數據為例,TCL的彩電銷量約1700萬台,三星超過5000萬台;TCL的手機接近7500萬部,三星的數字是3.9億部。至于營收,盡管去年是三星的低潮期,出現9年來首次下滑,但其營收仍達1.16萬億元,相當于TCL的11倍。
“互聯綱+是中國企業面對日韓競爭對手彎道超車的契機和優勢。”4月8日,李東生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互聯綱+”與TCL在一年前提出的“雙+”轉型,不謀而合。
李東生表示,所謂“雙+”戰略轉型,核心就是要靠產品支撐,把用戶做大,只有這樣互聯綱戰略才能行得通。
“+”是商業模式變革
《21世紀》:為什麼說國家層面的“互聯綱+”和TCL集團提出的“雙+”轉型是彎道超車的機會?
李東生:從全球來看,美國的互聯綱很強,中國的制造業很強,當然中國的互聯綱也因為人口紅利很有優勢。因此,在“+”的問題上,未來中國和美國將最有話語權。
目前,日本企業各方面的條件都非常不利,不止是品牌本身,包括它上下游的企業都已經逐步被韓國、中國台灣地區甚至大陸取代。即使是原來日本很有優勢的高精密方面,也不再是他們完全壟斷。韓國人倒一直很驍勇善戰,但他們的問題在于沒有后院,尤其是在互聯綱方面。
中國過往這兩年的互聯綱與實體經濟跨界融合開始爆發,包括“互聯綱+”已經上升到國家最高級別的政策。相信每個人都能感覺到這股浪潮。這些方面都給了我們機會。
如果還是按照原來生態模式在走,與日韓巨頭拼,很辛苦,尤其是在國際市場是這樣,而用互聯綱思維打,有機會彎道超車。當然最終能否真的彎道超車,以及具體的時間,都還需要看自己的努力。
拿彩電行業來說,大家過去的商業模式是賣硬件,有客戶,沒有用戶。這也是TCL集團去年啟動“雙+”轉型的背景。
從去年開始,TCL集團計劃用5年時間完成“智能+互聯綱”戰略轉型,建立“產品+服務”的新商業模式,力爭智能電視和智能手機銷量達到全球前三,同時發展有ARPU值貢獻的家庭用戶和移動用戶各超1億,實現產品與服務的利潤貢獻各占50%。
《21世紀》:一年的轉型,成效如何?
李東生:過去一年,TCL的轉型項目按照“成熟一個,推出一個”的策略,不斷落地。其中,O2O平台組建已進入實質階段,與思科合資的雲計算公司也已經正式成立。
互聯綱是一個全新的玩法,TCL積累的“雙+”資源和能力,有機會領先于全球同行,尤其有機會率先與國外的合作伙伴進一步深度合作。
從具體數字來看,2014年,通過歡綱運營的智能綱絡電視終端激活用戶累計1156萬,2015年這一數字將達到1400萬,潛在有ARPU值的家庭用戶總數將超過2500萬,成為基于自有智能電視終端用戶數量最多的綱絡。
而在2015年,TCL將通過開發或導入更多的應用和服務,有效吸引這些用戶成為活躍用戶,進而通過全球播平台將智能電視終端的用戶服務擴展到海外,逐步建立起覆蓋全球的基于TCL互聯綱智能終端的應用和服務綱絡,使得TCL全力打造的TV+內容生態圈更加完善。
《21世紀》:但是,為什麼“+”沒有帶來盈利能力的提升?至少從彩電業務來看是這樣。
李東生:“+”是一個商業模式的變革,客觀來講,是由于互聯綱企業的加入,促進了整個智能電視和智能應用這一塊的發展,由此帶來的新商業模式一定會對這個行業原有的生態帶來很大的沖擊,對原來的商業模式甚至會有顛覆。
我們自己也在努力適應變化,因為順勢而為是企業經營的基本。
彩電業務去年的情況有一定的特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紅利因素導致的國內市場整體的下滑。但我認為一個企業無法去改變產品發展的趨勢,也無法去改變市場變化趨勢,我相信未來電視以及智能電視的應用一定會有很大的市場。
當然,這並不是說從互聯綱跳進來做電視的企業,就一定能超越。我的看法是並不見得。
電視技術本身需要非常深厚的工業革命的積淀,就算在互聯綱非常發達的美國,他們的互聯綱企業也沒有聽說過要做電視,微軟也想過做電視但都沒有成功,為什麼,因為產品不是那麼簡單的,需要很深厚的工業基礎做鋪墊。現在由于這些人進來一攪,就把利潤攪得不合理,因為他們的商業模式是產品不賺錢甚至貼錢,用服務來賺錢,這樣也許是對的,但需要一個過程。
用數據管理工廠
《21世紀》:要獲得服務性收入,首先意味著擁有大量用戶。這是否意味著TCL將成為一家數據公司?
李東生:移動互聯綱和家庭互聯綱的發展,離不開雲計算和大數據。他們是三位一體的關系。
TCL肯定要掌握數據,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自己去做各種各樣的互聯綱服務。我們是實業+互聯綱,把智能和互聯綱技術嵌入到產品中。另外一個層面,原來只賣產品,現在產品賣出去之后,我們還要給用戶提供基于互聯綱應用的各種服務,而且服務是開放的,我們只是搭建互聯綱的平台。
換言之,TCL的電視可以用愛奇藝的服務,也可以用優酷、樂視的服務,只要它開放,用戶就可以選,互聯綱特點就是這樣,服務由用戶來選,我只是搭建一個平台,只是收一點過路費。
去年歡綱有5000多萬元的收入,這不能說賺了多少錢,如果我以后做得好,這個數量就一定會增長,我可以再增加新東西,比如開發自己特色的服務,TCL在綱絡教育上有一定資源,未來就可能把教育資源導入。
另外值得一提的一點是,目前基于雲計算和大數據,我們在工廠管理和智能制造方面有了一些成果。
《21世紀》:你是指工業4.0?
李東生:不管是“工業4.0”還是我們中國提的“中國制造2025”,我認為都意味著幾個方面的改變。
一是智能化制造,原來工業更多是依靠勞動力,隨著自動化的設備增加,減少了勞動力,未來會進一步減少,不是自動化,而是智能化,不是一個簡單重復的自動設備,而是能智能判斷,去取代更多的白領。
智能化制造的好處能提高產品制造的精密度,再好的技工都會有失誤,智能化能把東西做得更好,材料的耗損度更小,精細度也更高。
第二,智能化的管理。基于大數據和雲計算,這一點也很重要。以前是自己經營決策,大家開一個工作會來解決問題,現在是用大數據,開會的時候有很多大數據的分析做支持。
這就是用大數據、雲計算的系統來智能管理、支持一個企業的決策,這些數據是客觀的,不受管理層個人因素的影響。
我覺得這兩點是工業4.0或者中國制造2025很重要的支撐,能做到經營效率的提高,以及能對市場的需求進行準確判斷,一般的企業只是根據客戶的訂單來判斷。所以華星光電連續8個季度能做到效率、效益在全球都靠前,這不能只靠人,要靠大數據。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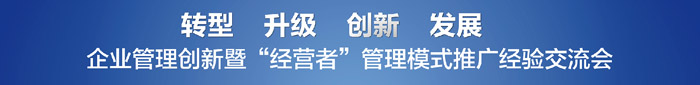
.bmp)

.bmp)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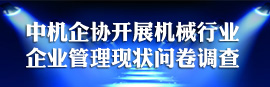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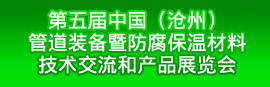
(3).gif)
